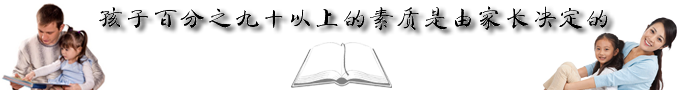甘肃省养不起莫高窟 数字化敦煌现还缺1.8亿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佚名
254窟 萨垂太子舍身饲虎 北魏 甘肃省养不起莫高窟 去敦煌采访研究院,时机不巧,正逢大小领导们即将动身去台湾学术交流,樊院长的助理说:“她这两天可忙呢,大小会议不断,还得准备去台湾演讲的报告,你就等着见缝插针吧。”谁知,头一天到达敦煌研究院,一大清早,就在院子里撞见一位瘦小的老太太,走路雷厉风行,速度接近小跑。向司机求证,“哦,精瘦是吧?那没别人,就是樊院长,这样的老太,这儿就一个”。之后问及一名讲解员才得知,樊老每天早晨7点,雷打不动要到洞窟景区门口溜达一圈,看看洞窟的情况,关照一下讲解员。照她自己的说法,就当锻炼身体。后来拍照时,她也是这么匆匆一路疾走,让记者任意抓拍,似乎小跑就是樊锦诗最为自然的状态。 王冀青认为,敦煌研究所的重点研究方向,很大程度上同院长的兴趣有关。前两任院长常书鸿与段文杰都是搞美术出身,而学考古学专业的樊锦诗显然更注重保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樊锦诗嘴里最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千古罪人”。她常说,“家里我可以不管,洞子保护不好,我就是千古罪人;有些人要把洞子搞上市,我要是同意,那也是千古罪人。” 71岁的樊锦诗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其实是上海人,采访中时不时露出两句上海话。她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来敦煌,一待就是40多年,研究院里有一处名叫“青春”的雕塑,据说原型就是她。 采访的时间原定于上午,却因为突如其来的会议延迟到了第二天下午,樊锦诗显得十分疲惫,说昨晚没有睡好。之前一天,开了一天的会,临行之前,还有许多工作需要部署下去,真的是大小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她开门见山就说:“我这里的事,绝不是幽默的表达,不睡觉都还干不过来。我那么忙,之所以还要接受你们媒体的采访,就想让你们帮我叫喊叫喊。” “叫喊”什么呢?两个字:“缺钱”。那是她眼下最急的事情。原本,数字化项目的总投资超过2.61亿元,现在通过跟政府反复交涉,最终答应由国家负担这个数字的70%,去年年底1.8亿元资金刚刚到位,这其中还不包括建造球幕游客中心的成本。樊锦诗说:“拍数字电影,不属于设施建设,国家不给钱。这样的话,算起来,我们现在其实还缺1.8亿元呢。国家所谓‘地方配套’的意思,就是还得要自己去找钱。” 采访间隙,樊锦诗接到一通听似是索要赞助的电话,她二话不说就严厉地一口回绝。“我一听费用,就啥都别搞了。我现在借债过日子,借着几千万呢。知名又怎么样?我才不管是谁。我说话直,他们好多人对我不感兴趣,说这个老太婆死倔死掘。”樊锦诗说,敦煌研究院旗下有18个部门,500多名员工,其中200多人不属于国家编制,国家不给一分钱津贴,全是门票收入养的。然而,去年的西藏事件、汶川地震、奥运会,再加上今年的新疆事件,都对敦煌的旅游业影响巨大。“本来,西藏、新疆属于一条线路的,中间少了两站,人家旅行团就不来了,我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甘肃省是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根本养不起莫高窟。” 采访后没几天,樊锦诗一行就动身去台湾交流访问了,临行前特意叮嘱助理安排记者参观了数字中心、图书馆、新建的实验室以及后山的防沙工程。 戈壁沙漠中的“数字中心”,想象中那是一个颇为“科幻”的地方。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人根本无法与2.6亿元的投资联系起来:仅有两台大型的苹果电脑在投入工作,两名年轻的女孩在办公室一侧看似非常不正式的工作区中用电脑拼图。她们是今年刚从兰州师范大学设计系毕业的应届生,正式入职才不久,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运用Photoshop软件,先把几十张仅20×30厘米真实大小、相同内容的图片手动拉伸重合,尽量克服照相机镜头造成的边缘畸变,然后再根据实况,把图片拼接成大幅的洞窟壁画。其中一名女孩说,大多数情况下,她们都是拼局部壁画,而后两人共同合作完成整个洞窟。目前为止,由她独立完成的完整洞窟只有一个,每天从早拼到晚,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才完成。照这个速度计算,与美方合作完成拍摄的40个洞窟的素材,需要20个月才能完成。好在两个女孩告诉记者,只有两台电脑同时工作的情况是暂时的,院方的计划是由她俩先完成第一批洞窟壁画的拼接,经过专家测试审核后,再购买更多的电脑、招聘更多的人手。 主管数字化工程的副院长王旭东表示,整个敦煌数字化工程,包括游客服务中心的3D影像制作,总工作量需要投入140个人,耗时三四年才能完成。根据市场经济的操作方法,这些工作最终将外包出去,研究所内部一定不可能录用那么多人手。至于外包是否能保证质量,王旭东没有在采访中正面回答。对于资金尚未到位的球幕放映厅何时有望竣工,王院长似乎也心里没底。 保护工作没有尽头 在樊锦诗数十载的任职期间,敦煌研究院在栈道改造、崖体加固防沙等地质工程方面都有很大进展,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基于开放的保护”的发展观。除了安置侦测洞内温度湿度的无线传感器,以随时关注洞内微环境的变化,轮流开放洞窟以及严谨的预约机制外,隶属于数字化项目的游客服务中心将是减短游客在洞窟中逗留时间的“最终解决方案”。 在景区中,经常可以见到一些类似于风车一样的风向检测装置,樊锦诗介绍说,沙子是颗粒状的,吹到壁画上,对文物影响很大,同时,沙丘是移动的,不存在固定的方向,所以观测风向在风沙防治中地位很重要。保护工作目前主要由地质工程专业出身的王旭东主管,其中包括40人组的修复中心、10人组的崖体加固项目、10人组的土建筑移植保护以及数字化工程项目。在王院长的安排下,记者驱车前往防沙现场,眼前是A字形的防沙尼龙网、植物林带、麦草方格、砾石铺压、化学固沙等重重防护,然而似乎都无法完全抵御大自然的威力。一些时间久的草方格已经完全被淹没在沙丘中,让人深深体会到保护工作之任重道远。 得知记者来自上海,王旭东很高兴地介绍起敦煌研究院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兰州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单位共同组建的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对壁画病害机理研究和修复已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如今除敦煌外,还承担起了新疆交河故城、宁夏西夏王陵、青海瞿坛寺和塔尔寺、西藏布达拉宫以及罗布林卡、萨迦寺等的壁画与土遗址保护修复工程。莫高窟的第85及98窟,正代表了目前国内壁画及洞窟修复的最高水平。大型晚唐洞窟85窟曾经在1997-2006年间被关闭了9年,直到最近才找到解决病害根子的办法,令王旭东如释重负。在修复现场,他说:“不同时代的洞窟,工艺不同,其矿物质的成分不同,解决问题的材料也就不一样。盐分是造成起甲的罪魁祸首,我们为85窟墙体脱盐,从而根本上阻止了病害的发展。85窟集中了许多相似洞窟的一系列问题,只要把85窟解决了,98窟的起甲和空鼓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而事实上,壁画的问题似乎是永远解决不完的。在参观洞窟的过程中,记者刚巧遇到一支查找病害的工作小组。昏暗的洞窟内,四五个女孩手执电筒,坐在小板凳上,分块区完成任务;她们的工作,是在放大比例的壁画画稿上,用不同颜色的水笔以不同的记号标示出不同性质的壁画病害,如空鼓、起甲、酥碱等等。大多数的壁画已经斑驳得难以辨识,而她们的标记工作则需要细微到1/4平方厘米的方格大小。这是一个中日合作的项目,专心致志工作着的日本女孩与中国女孩,很难辨别她们的国籍。小组的负责人丁淑君告诉记者,这些工作全部靠人力,且必须是对壁画很有研究的工作者,反反复复地盯着一个细小的画面,眼睛很容易累,加上秋季以后洞窟里特别冷,她们都需要穿上好几层衣裤,像她这样用眼睛“啃”一遍壁画,花的工夫基本就相当于临摹。即便现在有了各种数字化工具,这些针对实体的保护工作仍是不能停歇的,保护的工作根本没有尽头。 基于开放的保护 樊锦诗说,她所说的保护,包含了三层意思。数字化是其一,目的是主动地建立洞窟的档案,保存现有的信息,以备后人的研究。这个工作是“与大自然赛跑”,因为文物总是处于消退中,信息量越来越少,这不是人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其二是科学管理,像在这个山沟沟里,要吸引并留住专家人才,是不容易的,除了在体制上有所革新,感情上也需要培养。“你去问问莫高窟的讲解员们,他们都以这份工作为自豪。研究所真正是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如今人才已经形成梯队。”其三就是要开放,也要保护。莫高窟的旅游开放早已成为地方经济的一大支柱,旺季时每天平均接待2000人,最多一天游客达到8000人,然而洞窟空间狭小,过量的游客必定会对洞窟内脆弱的壁画和彩塑的保存构成严重威胁。 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前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李最雄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专家们曾比较过1906年与上世纪50年代同一壁画的照片,发现差异并不大,但同样是50年,到了旅游业开放的近些年,排除人为蓄意破坏的可能,壁画衰退的状况就较为严重。在洞窟景区的接待室里,墙上的显示屏上浮动着每个洞窟的二氧化碳含量以及相对湿度、温度的变化曲线,红红绿绿的,有点像证券交易所显示屏上的个股走势图。一项实验监测数据表明,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会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而相对湿度的反复上下起伏,是造成洞窟常见病酥碱的主要原因,温度上升和湿度增加都有可能侵蚀壁画。李最雄强调,对于造成壁画病害的各种原因,至今还无法做出很科学的定论,因为建立微环境变化与病害发展之间的参数关系非常困难,每一种颜料的成分都不同,其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也不同。 樊锦诗说:“如今我们将开放洞窟的数量定为30个,完全是根据旅行团的需求,一般旅行团的逗留时间约为两小时,看10个洞就走。藏经洞、飞天、各个时期的经典洞窟、雕塑以及大佛,每样都要面面俱到。此外,能接待几十人的旅行团的,那一定要是超过20平方米的大型洞窟。满足以上条件又没有病害的洞窟原本就不多,我们就争取每隔一段时间,轮流开放。” 在景区,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名警卫,严密监视着游客的举动。对于非开放洞窟,除非院长亲自签字的介绍单,否则警卫严格地不予放人。讲解员无法私自前往非开放洞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钥匙。一位讲解员小心翼翼地告诉记者,其实每个洞窟里都安装有摄像头,如果自己多带了游客,或者偷懒少导了几个窟,监控室里马上就能发现。旅行团参观洞窟还实行预约机制,从而错开时段,分流人群,尽可能满足洞窟的休息。 樊锦诗颇为自豪地说:“我们不会像有些县里的、地方上的单位,把一个古代遗产当摇钱树。前段时间开了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可持续利用保护会议,很多外国专家都盛赞我们做得好,除了数字化做得好之外,就是保护的同时开放——保护好的前提下充分开放,开放中间加强保护。” 说到开放,计划与数字化工程同步建设的游客服务中心,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开放,游客可以在球幕放映厅中尽情欣赏虚拟然而逼真的壁画和彩塑,无需担忧自己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只可惜,这个听上去无比美好的计划,暂时还遥遥无期,似乎只有等来有心人的慷慨解囊,才不至流于纸上谈兵。 对话樊锦诗壁画像我一样,转眼会从小姑娘变成老太婆 B=《外滩画报》 F=樊锦诗 B:数字化的工程已经进行了整整6年,目前的状况究竟如何? F:何止6年。你别看我们这个山沟沟,我们是很重视科学发展的。其实我们搞这个数字化,已经20多年了。1983年,我在北京首次见到计算机,大为震惊,就看到画面一个个蹦出来,像变魔术一样。当时,不知谁在我耳边嘟哝了一句,“什么都变,数字不变”。我们搞保护的,特别敏感,这句话当时就解开了我的心结。当时,研究所做洞窟的档案记载,使用的是胶片摄影和录像,然而,相片会褪色和变形,录像又会消磁和变质,没有一种可以永久保存的载体,只有数字不变。于是当时我们就琢磨着要搞一个数字化保存档案的工程。 B:这个工程是跟美国西北大学合作的,美国的技术移植敦煌后,有没有遭遇什么困难或进行什么改良? F:跟美国合作是后来的事,之前我们先在国内找,找了一个做遥感的单位合作,效果不大。后来才请来美国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技术人才,他们在这里也要学习。做遗产保护的,每到新的环境都要学习研究,没有完全有章可循的情况。他们在这里完成了部分洞窟的拍摄、拼贴及软件设计。用软件,我们可以搞标准颜色,颜色要通过后期校正,才可以完全做到一模一样。现在,美国人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们也把技术全部学到了。 做档案保存的难点在于,实物是五彩缤纷的,你要做有价值的保存,就要颜色保真、画面清晰,否则就是垃圾产品。壁画在退化,退化是必然的,今天做,同50年以后做,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你看我樊锦诗,刚来莫高窟的时候也才25岁,转眼就在这里待了46年了,人家说,你来的时候也是个小姑娘,怎么现在变成个老太婆了。这就是我在衰退,但是这种衰退是潜移默化的,就像你昨天见我,今天又见我,看似没什么区别,其实我已经退化了。对于文物,保护得再好,大自然的作用也会让它退化,所以保存要赶紧,要有价值地保存。
275窟 尸毗王本生 北凉 采访手记 在第85和98窟想象未来的数字敦煌 在敦煌莫高窟,第85窟和98窟是敦煌研究院眼下最引以为豪的两个“样板窟”。经过多年细致入微的修复工作,这两个曾受到严重病害侵袭的洞窟及其中的壁画、泥塑珍品,重新焕发出了光彩。 拿着樊锦诗院长的批条前去采访时,窟内为修复工程搭建的脚手架还未拆除,足有4层高,最高的一层,陪同的年轻解说员都不敢上去。但这却是最令我兴奋的,因为大多数洞窟里很阴暗,一般只能打手电,照到的范围有限,大一点的窟,窟顶高处即便手电光照着也看不清。而且洞窟低处由于人为原因和自然作用,一般破坏较严重,高处的壁画相对保存比较完好、变色现象也不那么严重,甚至有些飞天还保持着1500年前的鲜艳色彩,只可惜离得太远。而在85和98两个窟里,修复用的照明灯光还亮着,又能一路攀到离窟顶一两米的地方,不仅完整地看到全窟每一层面的壁画,还能细细观赏窟顶那密密麻麻、千姿百态的飞天、千佛与天王,真是极难得的体验。 矛盾的是,一方面,我颇为能有这特别的体验而得意,毕竟绝大多数游客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又觉得“独乐乐”之外也需要“众乐乐”,此等壁画精品,永远躲在阴暗的洞窟高处而得不到被人欣赏的机会,不免寂寞,就文化资源来说,也是很大的浪费。 好在,敦煌的数字化工程,虽然困难重重,毕竟在一步步地向前走。正如樊锦诗院长一再向我们强调的,数字化并不是要造一个“假敦煌”,而是与真敦煌形成资源利用上的互补,并且最大限度地帮助有自然生命期限的敦煌石窟久远地存在下去。 研究敦煌学的人,如我们采访的王冀青教授,自然对于敦煌数字化的重要性有切身的感受,那涉及各种极重要的学术资源的共享。 回想100年前,敦煌遗物刚刚引起轰动,敦煌学刚刚诞生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然而学者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在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共享与合作研究。斯坦因、伯希和、沙畹、罗振玉、王国维、内藤湖南、羽田亨等等国际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就材料与观点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借鉴与探讨,虽然有竞争,有时甚至颇为激烈,但并没有完全站在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上垄断各自发掘的敦煌遗物及其研究,相反,对学术成果的及时通报与通力合作大大促进了敦煌学在最初阶段的迅速繁荣。当时也还没有数字化工具,但学者们硬是通过临摹、抄写、编制目录、照片缩微胶卷等等(大概可以称之为“原始数字化手段”)实现了广泛的共享。 今天,当互联网和各种数字化工具已经极为发达的时候,共享与交流不是更应该成为敦煌研究的“主旋律”吗?可惜的是,无论我们还是国外的一些机构,对于共享依然存有较大的疑虑。这从王冀青教授在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遭遇(见本报下期刊登的王冀青专访),以及我们所见敦煌研究院对日本学者网络共享建议的“冷处理”,都可见一斑。或许现在谈完全的资源共享确实有些早,但共享是敦煌数字化工程的最终目标之一,我想是没有异议的。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对于我这样的非敦煌学专业人员、普通爱好者甚至一般游客,敦煌的数字化也有极大的好处。首先就是在匆匆忙忙的洞窟穿行之间被忽略的大量信息,数字化后能够得到极好表现,从而被我们“看到”。前述第85窟和98窟的上部与窟顶就是例子,一般你在莫高窟的参观过程中是看不到或至少看不清它们的,但是在3D的球幕放映厅里,一切都清清楚楚。 更进一步,我们目前还没有技术能力,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对敦煌壁画的实体做类似意大利《最后的晚餐》那样的全面修复,我们只是在做洞窟病虫害的修复,防止它们继续损坏下去,但还不能复原壁画当年的面貌。但是在数字化的时候,可以做这样的尝试,让游客在虚拟实境中看到那些壁画和泥塑在南北朝和唐代的原貌与盛况,体会它们当年真正的辉煌。带着这样的观感,再短时间地穿行于洞窟之间,我想所得一定会大大多于现在走马观花的匆匆一瞥吧。

·上一篇文章:艺术品修复作坊步入殿堂?中国油画进入修复时代
·下一篇文章:拖欠制作纪念册及邮票费用 陈逸飞遗孀已被起诉
转载请注明转载网址:
http://www.zjjr.com/news/artxw/0912279344341307AKF84752A94AH33.htm
相关内容
|
佚名 | |
|
佚名 | |
|
冯志军 | |
|
佚名 | |
|
张玉洁 | |
|
张漫子 | |
|
冯志军 | |
|
佚名 | |
|
佚名 | |
|
高康迪 杨艳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