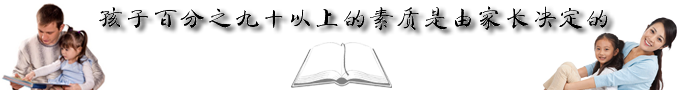中国校园欺凌现象调查:欠缺整套儿童保护系统
来源:学习力教育智库 作者:佚名
中国欠缺一整套儿童保护系统
“所有事件显示,我们对家庭和校园里一些常见问题太缺乏意识了。”童小军说,“曝出来一件事,大家便只关心这一个问题,所有的看法都是支离破碎的。事实上,校园欺凌、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等问题,都是整个儿童保护系统的一部分,中国目前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形成一个儿童保护体系。”
美国的校园欺凌现象也很严重,但社会对这一现象给予极大关注。除了联邦和各州政府加强立法外,还要求各学校为学生提供举报校园欺凌事件的渠道,并对欺凌者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2013年,日本参议院通过《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此外,文部科学省增加了学校辅导员和护理员的数量,扩充学校咨询机构及校园社会工作者的规模,并设置24小时不间断服务咨询电话,以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
澳大利亚专门建立了政府组织和网站,帮助学校解决欺凌现象,同时将反对欺凌、骚扰、歧视、暴力的教育列入教学大纲。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是国家命名的“反欺凌日”。
“很多人说中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立法其实仅仅是这套系统的第一步。”童小军说,“这套系统不仅要有立法,还需要一个庞大的专门做儿童保护工作的社工队伍。”
童小军介绍,美国的中小学均需有驻校社工,如果社工人员不足,也可由护士或心理医生替代,但必须接受专业的儿童保护工作训练。“儿童保护要由专业儿保社工来做,试想,如果学校老师出现了打骂学生的情况,学生敢去找其他老师寻求帮助吗?但如果孩子向儿保系统寻求了帮助却没有得到解决,就要向儿保社工和所在机构追责。”
童小军还认为,中国学校普遍对校园欺凌行为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儿保社工应该由政府强制向学校派驻。她的一个同学曾想到某个学校做相关研究论文,校方的直接反应是:你要揭露我们学校的黑暗面。
但也有些民间机构,开始自发地在中国校园进行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
国际计划是一个以儿童为工作对象的人道主义国际组织。2011年开始,国际计划(中国)在陕西省4个县域16所学校中,开展“无忧校园”项目,以减轻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行为。国际计划(中国)的儿童保护项目经理管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对校园欺凌包括三方面:预防、早期干预和欺凌个案应对,国际计划的项目主要侧重于预防和早期干预,所采取的办法是在校园里开展反校园欺凌的宣传,告诉孩子们自我保护的办法,以及鼓励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信。
每个暑假,项目组还会抽取某个班级的一些学生,举办10天左右的夏令营,通过心理干预法,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教会他们怎样交朋友,怎样与他人有效沟通,以及出现暴力冲突时该如何解决。“之所以选择一个班级的孩子,是希望能够每次集中改变一个班级的气氛。”
管桢说,在夏令营里,往往可以通过观察发现有欺凌或受欺凌倾向的学生,事后通过家访等方式进行早期干预。该项目还针对老师做应对校园欺凌的专门培训。
广州市海珠区“青年地带”也于2012年启动了第一期反校园欺凌服务项目。他们与政府合作,对海珠区12所学校每校派驻两名社工。“国内很多学校都比较避讳校园欺凌话题,但邀请我们进驻学校的领导比较开明,他们不掩盖,选择应对,这是项目能够开展的主要原因。”郭欣欣说。
“青年地带”十分强调驻校社工与学校老师的不同。“我们强调社工和老师的区别,这是两个专业、两种职业。我们会让学生叫我们Miss或阿sir,而不是老师。”郭欣欣说。
但项目最初开展时,校方对于社工能起到的作用仍有疑虑。被拉入帮派组织的学生李亮成为打开工作的钥匙。帮派成员借口“带他去见老大”,逼他回家“拿”钱,被家长发现。李亮陈述了原由,家长立即报警,在社区警察的协调下,双方家长共同讨论解决方案。
“青年地带”社工主动参与到家长会议中。社工了解到,李亮父母工作繁忙,经常不在家,忽视了孩子的成长。社工将李亮带入到戏剧表演活动中,经过一段时间磨合,李亮主动要求在戏剧中扮演欺凌者,并且参与度越来越高,也对欺凌行为有了新的认识。之后,李亮结识了新的朋友,并利用周末一起去做志愿服务,和以前的帮派彻底脱离了关系。
目前,这12所学校都提供了专门的社工服务场所——社工站。社工站以绿、黄等清亮颜色为主,设置有图书阁、桌游区等,吸引学生在课余时间前来。
郭欣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午休和放学后是社工站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有的下棋,有的玩桌游,更多人在聊天。“很多是他们在班里不方便讲的话,社工陪他们聊天,也陪他们玩。”驻校社工的工作还包括帮助召开主题班会,个案辅导,召集由欺凌行为双方参与的会议以了解其背后的根源,以小组形式培养孩子们处理压力、应对矛盾的社交技巧,培养自尊感等。
郭欣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对校园欺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一大批专业人员,同时需要开拓孩子们交流的渠道。“青年地带”正在筹备开发一个名为“校园零欺凌”的APP,希望能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青少年、家长和教师的互动,普及预防及应对校园欺凌的信息,实现对校园欺凌真实情况的评估。
那些年,我参与的校园欺凌事件
从一个被扇上百个耳光的“乡巴佬”,到用烟头烫别人的“大姐大”,一位
曾经的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制定了周密的复仇计划,成为施暴者。若干年后,
反思曾经的遭遇,她说,不要试图用成人思维,去理解孩子的世界
本刊记者/刘子倩
24岁的韦怡对视频中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9个十几岁的初中女孩围殴一名同龄女生。打人的女孩穿着高跟鞋,化着浓妆,戴着墨镜,超出了学生的装扮。她们轮番上去扇耳光,揪头发,脚踹腹部。被打的女孩被踹倒,跪在地上,双手捂着已红肿的脸。这段视频后来被证明是发生在江西永新县的一起校园暴力事件。
韦怡曾是校园暴力的亲历者,从一个被扇上百个耳光的“乡巴佬”到用烟头烫别人的“小太妹”,绝情的暴力、绝望的求助和绝命般的自杀,这个受害者最终选择制定周密的报仇计划,摇身一变为一呼百应的“大姐大”。不到两年时间,她“完美复仇”,代价是三年内换了五所高中,以及勉强上了一所艺术类高校。
不过,在韦怡看来,最大的代价还是难以复返的青春。
来自“新新人类”的威胁
韦怡长着一副标准的瓜子脸,大眼睛,说话温婉可人。她曾是一家电视台的项目经理,负责一个十来人的小团队。最近,她刚刚跳槽,到广州一家上市公司做公关。无论到哪,同事和领导对这个“乖乖女”都关照有加。
只有男友知道她的“秘密”。
1991年,韦怡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军人家庭。从记事起,她就“寄宿”在乡下奶奶家。父亲在部队服役很少回来,母亲在城市里工作,每个月回来看她一次。同样住在奶奶家的堂妹,与她年纪相仿,性格相似,自然成了她最好的玩伴。
或许是为了弥补在农村成长的缺陷,到了上学年龄,父辈们将她俩送进市里最好的私立学校,姐妹俩被分在了一个班,每人一年学费8千多元。那是1997年。
但重金难以填平城乡教育的鸿沟。她们发现,同学们各有所长,能歌善舞,而她俩身无长物。更要命的是,她们过重的乡音,身上穿的奶奶做的大红挂绿的衣裳,都成为同学们的笑柄。“我俩成绩都很差。三年级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韦怡说。
同学们给她们很快起了外号“乡巴佬”,一叫就是六年。调皮的同学还组织公选了“班级四丑”,全班76名同学匿名投票,韦怡和妹妹高票当选。她们因此又多一个绰号。同学们有意无意地孤立她们,但姐妹俩互相做伴,也不太在乎。“学校给我的是一个假象,我只要有妹妹,就不需要交朋友。”韦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韦怡也有在乎的事情。同学们在班上炫耀,父母给班主任送了什么礼物,换来老师什么样的关照,韦怡也希望如此,便求父母送礼。“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父亲不容置喙地回答。此后,她便很少再和父母交流学校生活。
2003年,韦怡考上了省重点初中。一个年级近两千人,她每次都能考进前50名,最好一次排名全校第三。在成绩即一切的中学校园,这个自闭寡言的女孩成为班长兼团支书。
跨入中学阶段的90后,很快成为一代“新新人类”。这个1990年代的台湾词汇在21世纪传入大陆后,迅速被大陆“新新人类”刷新了内涵。他们的时尚法则是:三天两头翻新奇特的发型,和怪异乱搭的服饰。
韦怡还记得,初二时,班里有几名“混社会”的小太妹,喜欢穿裆及膝盖的吊裆裤,用烟熏烫或玉米烫,做出头发根根直立的效果。她们在课间大谈与男友做爱的细节,甚至分享堕胎的痛苦。“那时都还没有是非观,大家感到的都是新奇。”韦怡回忆说。
班里的5个刺头儿很快和韦怡结下了梁子。韦怡是班长,会将她们迟到、旷课以及不交作业的情况向班主任汇报。在学校,向老师打小报告的人似乎都会受到鄙视。但最为致命的是,班主任会在韦怡报告后让她们请家长。这对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们,意味着极刑。
她们开始挑衅韦怡,在班里大声谩骂,或是闲聊时冷嘲热讽“管闲事的人没有好下场”,“我在外面认识人,想什么时候打她就能打她”。那时,“打同学”似乎成为一部分同学的“潮流”。韦怡班上一个叫郭美玲的女孩常鼻青脸肿地来上课,同学们议论,是校外人打的。若干年后,她改名为郭美美,并因炫富让中国红十字会饱受争议。
这一年,还有一个名叫马家爵的大学生因为打牌争执,杀死自己的4名同学。2004年的一项校园暴力问卷调查显示,10.5%的学生曾面临校园暴力的威胁,94%的学生认为,在社会中自身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但韦怡没受影响。她的逻辑是:大家都是同学,更何况我是为了帮你进步。所以,当一个小太妹用手指着她威胁说“你以后说话给我注意点”时,韦怡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她后来回忆,那时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和“校园暴力”扯上关系。
第一次遭围殴
距中考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某天,一位同学偷偷塞给她一个纸条:放学不要一个人走,让你爸来接你。神经大条的韦怡并未在意。
因为高考占教室,学校提前放了学。韦怡还没来得及收拾书包,那5个女生就把她围住,要带她出去谈谈。她们拽着韦怡出了学校。“我当时腿都软了,一句话都不敢说。”韦怡被带到距学校步行十多分钟的一个水坝工地。
“你知道为什么要找你吗?”对方问。
她摇摇头:“不知道。”
“好,不知道就打到你知道。”就像发生在江西永新的视频一样,5个女孩轮番扇韦怡耳光,一共扇了5轮,平均每人打了十多个。
韦怡的脸顿时全是火辣的灼伤感,嘴角流出血来。但出人意料,她没有哭,也没有求饶。“我自尊心强,当时觉得,被打已经很丢脸了,再掉眼泪那就更丢人了。”
最后,她被打蒙了过去,再次清醒时,打她的女孩们已经走了。她的眼泪喷涌而出。尽管离家步行只要五六分钟,她还是打了出租车。她吓得浑身发抖,连书包都没顾上拿。
可是,当她浑身裹着泥、衣服上布满脚印、头发凌乱、嘴角带血地出现在家里时,军人出身的父亲的第一反应竟是机关枪般地训斥:“哭什么哭?还有脸哭?”“为什么连帮你的同学都没有,为什么不打别人,你想过没有,你这都是自找的。”
韦怡没吃晚饭,躲在房间从晚上7点一直哭到夜里9点。她越想越害怕,捂着红肿的脸冲到客厅:“明天送我上学,然后报告班主任行吗?”父亲拒绝了,“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父亲以部队的生活经验作为判断依据:部队里打架流血很正常,被打只能说明没本事。
韦怡当时的理解是,她们是打算把初中3年的仇恨在毕业前发泄,毕业之后就两不相干。在家养了几天伤后,韦怡才去上学。班级里的气氛明显不一样了,她感到同学们都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却没人来安慰她。上课,她很难集中精神;下课,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她以交作业为由躲在老师办公室。“我没有告诉老师,因为怕她们再打我,真的怕了。”
但第二次暴力事件很快发生了。上学第二天中午,5个姑娘要求她在放学前凑够500块钱,否则后果自负。一下拿出500块钱,对一个初中生来说不是小数目。“我当时想,一下拿出500块,非偷即抢,那我还是宁可选择被打吧。”
她“如愿以偿”了。地点还是大坝工地。拳打脚踢过后,姑娘们说第二天放学前要收到1000元,否则没完。“你们别想了,我爸妈不可能给我那么多钱。”韦怡嘴硬,“你们想干什么就抓紧,六点半回不到家,我爸就会来找我。”当天中午,她已请妹妹帮忙通知家人,放学后来接她。但这句威胁话换来的是一百多个耳光。
韦怡身上的八十多块钱都被抢走了。她狼狈地走回家。父亲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她回到房间,开始了与父母的冷战。“我当时觉得,可能我并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事后她才知道,妹妹也没有转告她的请求,理由是“去救你也来不及了”。
“我决定去死”
韦怡不再哭了。无助和无法逃避之后,她选择了忍耐。但是,1000元的威胁并没有作废,她第三次在放学后被架到了工地。
这次除了班里的5位“侠女”,又多了5个校外女生。她们化着烟熏妆,穿着高跟鞋和吊带衣,脖子、胸前、小腿上都有文身。校外女生显然是老江湖。
一顿殴打折磨后,10个女生离开时,还抢走了韦怡的小灵通。韦怡一瘸一拐地走到附近小卖部给家里打了电话。母亲看到女儿的惨状泣不成声。在医院,医生用消毒水清洗伤口,拿镊子将玻璃渣一粒粒夹出来。韦怡疼得边哭边骂:“我一辈子都恨你们,不要想让我孝顺,你们死了我都开心。”母亲一声不吭,倒是医生在一旁帮腔:“哪有你们这样的家长,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第二天,韦怡的腹部变成了紫黑色。
母亲终于向老师说明了情况,并给韦怡请了几天病假。但班主任的态度模棱两可,看起来不太想直接处理这件事。同班的5个女生中,有一个与韦怡家同住一个小区。母亲找到了她的家长,对方登门道歉,还赔偿了5000块钱。不成想,这成了韦怡下一次遭遇的祸根。
休息数天再回到学校,距中考只有十几天,韦怡对考试彻底失去信心,上课就想哭,晚上12点还睡不着,被打的场景就像电脑病毒,强行按顺序在脑海里播放。
但没过几天,那个赔了5000元钱的“女汉子”又跳了出来,扬言要制服韦怡,找回父母赔钱的面子。“我们今天还要打她,所有人都要在场,谁不去我们就打谁。”她在班里公开宣布。
最后有三四十名同学出现在工地,以女生为主。5个女生要求每人至少扇韦怡一个耳光。一个同学反对:“大家都是同学,何必这样呢。”刚说完,她就被甩了十多个耳光。
大部分打韦怡时都是装装样子,但也有人下狠手。“直到现在,这都是我人生最为屈辱的一幕。” 韦怡高声叫道:“你们会遭报应的,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对方一脸不屑:“报应赶紧来吧,我们这是替天行道。”韦怡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了。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她只能看到嘴动,听不到任何声音。
同学们渐渐四散,留下韦怡孤零零的一个人。茫然四顾,她不知道是该回家,还是留在工地。除了被打的屈辱,她心里不断冒出来的念头是:明天会怎么样?后天呢?
她站起身,没有回家,而是朝着大坝下的江边走去。她决定去死,不再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
她一步步走入江中,水漫到腰部时,突然感到有两只胳膊将她抱住。原来,同班的一名男生没有离开,一直跟着她。韦怡与男生厮打起来,哀求对方放手。尽管被呛了几口水,男生最终还是把她拖了上来。
男生把她送回家,讲述了整个过程。韦怡第一次看到严厉冰冷的父亲惊慌失措的样子。虽求死而不得,韦怡似乎依然从这个仪式般的行为中获得了某种新的能量。那个晚上,她在日记中宣布——她要复仇,并列出了详细计划:第一步,成为有势力的人;第二步,存钱,有了钱才能有小弟;第三步,将10倍的耳光一一还回去。“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这一年,在中国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中,韦怡不是最惨的。甘肃会宁县四名初三学生围殴一名男生,其中将长刀插进受害者颅脑内12厘米。2006年似乎也成为校园暴力高发年份,媒体甚至在年末盘点全年的二十余起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也是在这一年,台湾地区专门开通了反霸凌免付费电话,提供24小时申诉服务。
“打人居然很爽”
靠着“吃老本”,韦怡考上一所市重点高中。她的成绩本来可以考上省重点高中。
暑假里,韦怡启动了第一步计划。她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本市的百度贴吧里,与各种人搭讪,也观察、考量着每个人的身份。她注意到一个女网友的发言,总会有很多人追捧,在吧内一呼百应。“她的人脉应该很广。”
韦怡决定结识她。她主动攀谈,向她献殷勤,并渐渐学会了花言巧语,察颜观色。上了高中后,她一改从前自闭的生活习惯,广交朋友,每个月家里给她1500元住校生活费,她省下来请同学们吃饭。人漂亮,性格开朗,出手大方,她很快成了年级的焦点。但由于高中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为了“复仇”的人脉拓展不至于半途而废,韦怡常凌晨翻墙出去上网。开学不到两个月,她就被学校开除了。
自杀事件之后,父母一直对她心存愧疚,被开除后的韦怡开始为所欲为。韦怡与那个呼风唤雨的女网友见面了,把自己省下的钱都花在她身上,甚至深夜给她送夜宵。韦怡这时知道,她是一个酒吧坐台女,那年21岁,韦怡也刚满15岁。韦怡认这位网友为姐姐。
姐姐带着她游走各种场子结交朋友。虽然身份是坐台女,但韦怡能感到姐姐并不是是非不分。姐姐有时会吸食大麻和打K(吸食K粉),但从来不让韦怡碰,有朋友想灌韦怡酒,姐姐都会帮她会拦下来。“我觉得她是真对我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韦怡与姐姐、朋友在KTV唱歌,居然遇到了初中打她的那5个女孩中的一位。“给我跪下说100声对不起。”韦怡招呼包房的二十多人把她围住,瞪着对方叫道,就像当年她们瞪着自己一样。对方完全没有了当年叱咤风云的样子,低头跪在地上开始说“对不起”,每说一句,周围的人就数数,一直数到100。“那时还下不了手。”
这个女孩显然不服,事后叫上曾让韦怡跪玻璃的校外女孩与她约架,地点仍然是那个水坝。对方只带了四十多个高中生,而姐姐却帮韦怡叫了六十多个夜店看场子的哥们,刚一碰面,还未动手,对面就有一半人被吓跑了。
“妹妹,是你亲自动手,还是我们上。”一个壮汉问韦怡。韦怡摆出大姐大的派头:“把棍子给我。”三个曾经给韦怡的双腿留下伤疤的女孩跪在她面前,她抡起棍子就打,直至三个人抱头求饶。姐姐这时候站了出来,打了每人三个耳光:“这是我妹妹,要再找她麻烦,我奉陪到底。”
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从天而降,韦怡终于感到可以充分自由地呼吸了,所有曾经消失了感受瞬间回到了她身上:自尊、成就与兴奋。她觉得整个人都满血复活了。
“那次打人之后,我感到很爽,觉得这种生活令人羡慕,就算不上学也无所谓了。”韦怡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为了感谢这些朋友,韦怡请大家去KTV消费,一共花了7000多块。但韦怡暗暗给自己定了规矩:只针对那些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绝不伤及无辜。她正式成为了“混社会”中的一员,并以文身作为投名状。她在锁骨处文了一个精灵,寓意涅槃重生,又在腰部文了坐台姐姐的英文名字,以示铭记和感恩。
“复仇计划完成了,那就学习吧”
韦怡的父亲转业后进入商界,手头还算宽裕。家人花了5万元,将她送到另一所市重点。只过了3个月,因为与老师打架,韦怡再次被开除。“爸妈彻底对我失望了,觉得我需要看心理医生。”
但韦怡却巴不得这样。她逐一寻找“黑名单”上人的下落,继续未竟的复仇计划。她对此也驾轻就熟。如果是约架,她就带上三四十人赴约,若是去校门口搞突然袭击,只需带十几个帮手即可。复仇现场,她也不再纠结,一阵耳光,连打带踢后,她就袖手旁观,交给打手们处理。当年对她颐指气使的姑娘们,往往没打几下就哭着求饶。“真没我有骨气。”韦怡一脸不屑。
那时开始流行用烟头烫。有打手要烫对方的脸,韦怡制止了。“烫手就可以了。”她指示。如今,韦怡觉得那时的自己虽然有些嚣张,但内心还算善良。
高二时,她去了第三所高中,她浑浑噩噩地混了过去,快到高三时,家人再次花重金将她转到了一所省重点高中。这个社会经验丰富的女孩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学校把花钱来的学生分在一个班,她居然跟男友成了同班同学。
但奇怪的是,满身风尘气的韦怡开始看不惯班里的氛围。同学们在课间玩炸金花赌博,起步就50元;有的晚上去泡吧还会打K;几个官二代傲气十足,每天专车接送。17岁的韦怡渐渐脱离了以“复仇”得来的快乐,被一种巨大的心理空虚所笼罩。
她向家里主动要求再次换学校,到省会一家培训机构学画画,准备报考艺术类院校。“那时突然觉得复仇计划完成了,人生没了目标,连玩都变得没有意思,那就学习吧。”半年后,韦怡勉强被一所艺术类院校录取。
上大学后,韦怡开始反思这段混乱而无序的生活。但她发现,十四五岁的孩子的世界,是无法用成人的理性思维来认识的。虽然她如今仍无法理解,只因她完成老师交付的工作,同班女生就用暴力来对待她,但之后几年的经历使她发现,那个年龄的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丛林社会,“强者才被羡慕,弱者不值得同情”——人人都有成为“强者”的渴望,如果不能在学习的任何一个方面成为强者,孩子们也不会拒绝依靠暴力成为强者。因为,他们所被灌输和所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一个世界。暴力行为会随着打人后的征服感和成就感不断升级,幼稚而无知,使暴力变得更加残酷。就像她自己一样——依靠暴力为自己讨回了她所认为的公道。
但相比校园里的暴力,韦怡感到更刻骨铭心的,是父母的冷漠。他们认为这只是“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质问她“为什么只打你,不打别人”,这让她感到自己被所有人讨厌,没有人关心她、爱她。直到工作后,韦怡才鼓起勇气问父亲,为什么在她最需要家庭帮助时那样冷漠,父亲总是转移话题,最多只说过三个字:别想了。
许多经历过校园暴力的人终身活在痛苦的记忆中,但韦怡是幸运的。她渐渐走出了校园暴力留下的心理阴影。她远离了曾经发生这一切的城市,并渐渐与家人、社会和过去的自己达成了某种和解。
如今的韦怡,温柔可人、工作稳定,正筹划着组建家庭。她说,如果她的孩子重复她的经历,她会选择先报警,再通知学校和对方家长,三方共同当面解决问题。“我会对孩子说,无论你遇到什么,都要告诉妈妈,妈妈会永远站在你身边,成为你面对一切的勇气。”
(应受访者要求,韦怡为化名)
校园欺凌:现实版的残酷青春
施暴者、受难者和旁观者是校园欺凌中的三方。严重的欺凌可能改变受难者
的人生;但在欺凌发生之前,反倒可能是施暴者更可怜些;旁观者则是个
庞大的群体,可细分为欺凌的跟随者、欺凌的推动者、欺凌的遏制者和局外人
文/曹红蓓
良家文艺青年以往多在电影里看到虚构的残酷青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晃荡的人像,破碎的光影,似乎也像镜子一样照出自己的内心。
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影像频现网络,拍的却是生活中的真实。画面里一群少年或少女向一个受难者施暴,受难者任凭凌虐毫无反抗之意,看客发出哄笑并充当摄像师。这样毫无艺术感的青春影像见诸网端后,终于激起了人们的不适和不安。此时,距美国37个州颁布校园反欺凌法才过了7年。
还是要先界定一下概念,当我们在谈论这些视频和事件的时候,我们谈论的重点不是简单的校园暴力,不是简单的攻击或戾气,而是欺凌。两个人打架,或两拨流氓打群架,都不是欺凌,而是较量。只有在实力悬殊,以绝对优势恃强凌弱,以多胜寡的时候才是欺凌。而欺凌,除了殴打以外,还包括敲诈勒索、语言暴力,不碰身体也可以欺凌。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挪威心理学家就已经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到了1983年,北欧有三名校园欺凌的受难者相继自杀,校园欺凌问题才开始成为心理、教育学界关注的重点,30年来热度不减,成为发展心理学里面经典的研究问题。
校园欺凌的问题,不是中国现阶段发展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它在所有的青春里一直显著存在着,只不过刚刚被我们看到、承认而已。当然,如果详细比照,中国现阶段的校园欺凌问题中,有哪些部分是反映了当下国情,应该也有很多研究空间。
以西方的数据来看,85%的女孩和80%的男孩报告在学校受到过至少一次欺凌,10%~15%的学生曾经欺凌过他人。日本一年中所报告的校园欺凌事件有2万多件。校园欺凌如此普遍,在成为一个问题之前,也曾一度被人当作青春的一个部分,甚至一种成人礼。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文化、时代里都存在,确有一定的生物和心理基础。它是一部分人格发展有潜在缺陷的青少年在获得了身体的力量之后,将人性中原本的脆弱和焦虑的部分表达出来而已。
施暴者、受难者和旁观者是校园欺凌中的三方。从研究和干预的角度看,对每一方的观照都至关重要。
看了视频的人都会认为受难者可怜,施暴者只有可恨可诛。严重的欺凌诚然能改变受难者的人生,将他们从此送入可怜人的行列,但在欺凌发生之前,真实的情况反倒可能是施暴者更可怜些。
研究显示,有50%的施暴者来自有虐待行为的家庭。单纯的施暴者,指那些总是可以成功有效地运用攻击,同时从不被别的孩子欺凌的孩子,是成年后反社会人格的有力候选人。他们通常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最典型的特点是没有共情能力,不能感受别人的痛苦。在实验场景中,播放一个人手指被针刺的镜头,一般人会情不自禁的皱眉头,仿佛能感受到被刺人的痛苦;而没有共情能力的人就没有这种反应,好像一只破败的膝盖没有膝跳反射。没能发展出共情能力的孩子,通常在极早期的养育中经历过严重挫折,或者本身是家庭暴力的长期受害者,都是一些非常可怜的孩子。
单纯的受难者,指那些只是被欺凌而从不欺凌别人的孩子。他们个性退缩、顺从,有一部分自身带有一些特点,如来自破碎的家庭或身体有瘦弱残疾等特异性。他们屡被欺凌后容易变成习得性无助,在明明有机会反抗或逃走时也选择坐以待毙,就像我们在视频看到的,几乎都没有一丝的反抗。对于受难者来说,被欺凌的经历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是成人礼,反而是一种毁人礼。本来他们长大以后也许会是一个低调温和而有所成就的人,结果只能终生生活在自卑和习得性无助的烂泥潭里。
在校园欺凌的情境中,还有一类角色,同时兼具了施暴者与受难者的双重特征。这个角色的心理问题一般要轻于单纯的施暴者,但重于单纯的受难者,而且在被欺凌了以后,比单纯的受难者自杀风险更高。他们的个性冲动,敏感,易激怒,容易对别人的行为作出敌意归因,而且反抗得毫无策略,他们先是做出过激又无效的攻击反应,然后反给自己招致欺凌。心理咨询有助于他们状况的改善,但是需要做很久,或许好几年。
旁观者始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又可以细分为欺凌的跟随者、欺凌的推动者、欺凌的遏制者和局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江湖要混,旁观者的分流比较依赖于群体的动力。群体总是奖赏那些他们认为他或她应该做的行为,而惩罚那些与群体标准不符的行为,其中的个体只有望风而动。对校园欺凌的干预,从这个角色入手最容易显效。而对施暴者、受难者、施暴/受难者的心理拯救,亦是刻不容缓。
·上一篇文章:贫困地区小学的“数字老师”
·下一篇文章:“起跑线恐慌”并非矫情
转载请注明转载网址:
http://www.zjjr.com/news/jygc/15731123251CCFHK9BEE1BBB441A1FH.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