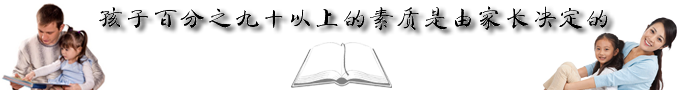安徽毛坦厂中学成高考圣地 墙外香灰1米多高
来源:中国校园文化建设网 作者:陈璇
在校领导看来,毛中的门道,“一点儿都不神秘”。它在校园里几乎随处可见,被赋予各种形式向人们展现——可能是学校花坛里写着“肯吃苦才能代代成才,守规矩方可日日进步”的宣传牌,也可能是教室墙壁上直截了当的“为了大学,拼命吧”的励志标语,或者是老师们爱说的那句口头禅“两横一竖,干!” 这一切都成就着毛中的高考“神话”。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毛中只是一所不为人知的山区学校,而且它随时面临着和其他乡镇中学类似的命运——在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背景下,逐渐衰落。 如今的毛中,演绎着一个“逆袭”的故事。这个地处大别山余脉的中学,正在修建田径馆和游泳馆,还在操场上立起一块巨大的LED电子屏幕。毛中的老师自豪地说:“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一块电子屏幕。” 有人认为毛中是“高考圣地”,也有人说它是“地狱”,隐喻着中国高考的畸形和异化。在毛中经受过锻造的人,在网络上宣泄着对母校的复杂情绪。有的人对它很痛恨,也有人说:“对毛中充满感激。” 信奉毛中“神话”的家长和学生,还是在使劲儿地往那扇门里挤。很多人认为,只要一脚踏进毛中大门,就意味另一只脚踏进了大学。 8月的最后一天,一位六安当地人帮着一对来自庐江县的农村夫妻,往复读班的教室里硬塞进一张黄色课桌。讲起这事时,他咬着牙,双手在半空中环抱,比划着为挪动那张课桌费劲的样子。 这位不付重托的朋友,在那对夫妻面前,拍着胸脯说:“放心吧,进了毛中,你们女儿来年高考一定能涨分。” 安徽当地人认为,托关系将亲友的孩子送进毛中,“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现实是,也有好不容易挤进毛中的学生,在这里呆了一两天,就哭喊要逃离。 复读班开课后第二天,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个子女生站在教室门外抽泣。她拖着哭腔向一位中年妇女哀求道:“妈,我真的受不了。我一看到,那么多书,太恐怖了。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不读了,不读了。” 穿着套裙、脚踩高跟鞋的母亲,脸涨得通红,恨恨地说:“你不读?你为什么不读?这么多人不是都在读吗?你知不知道,为了能让你上这个学,我已经烦透了!” 她伸手将眼睛哭红了的女儿拽到教学楼角落里,指着楼道远处,甩出一句话:“你要是不读了,直接从这儿跳下去。” 郑汉超的父亲有些担心,自己的儿子是否也会成为“逃兵”。这个在氛围自由的国际学校里呆惯了的男生,已经开始抱怨“毛中太苦了”。 但是,“就像放进炼钢炉的铁块,不可能再伸手往回捞”。平日里娇生惯养的儿子,“在这里吃苦,受委屈,甚至个性被压抑,统统可以接受”。 “其实,这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但也是合理的存在。是体制错了,还是勤奋错了?”这个殷切盼望儿子考上大学的父亲反问。 郑汉超还算“争气”,他把iphone5扔进抽屉里,换了一个在镇上买的款式老旧的手机,不能上网,只能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 这个在微博上拥有11万粉丝的男生想起,应该跟关注自己的人们短暂告别一下。他又掏出手机,发了一条微博:“你们一直抱怨这个地方,但是却没有勇气走出这里。9个月,咬咬牙,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却有着同一个目标,请等我回来。” 不过,郑汉超并不想告诉朋友们,“这个地方”是毛坦厂,一个被人们视为诞生高考“神话”的地方。 从以“三线”厂为荣,到以“毛中”为荣 9月初,毛坦厂镇政府办公楼的玻璃门上,贴着大红色的高考喜报。 官方对外展示的地方简介里,毛坦厂中学占据着最靠前的段落,高考成绩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处笔墨。 对于这个安徽的山区乡镇来说,教育是当地发展布局里的一张王牌。用杨化俊的话来说,学校是毛坦厂发展经济的“引擎”。 这台“引擎”发动起来,给这个镇子注入看得见的商机。数以万计的外地学生和陪读家长涌进毛坦厂,催生了当地特色的“房地产经济”。 这些外地的房客,大多住在书店、超市或者农贸市场等的商铺楼上,为毛坦厂当地居民带来一笔稳定而又可观的房租收入。 陪读家长大多抱怨:“这里的租金太贵了。”目前,镇上对外出租的房子,最便宜的租金一年大约四五千,最贵的达到两万多元。在当地,“一家本地居民靠出租房,一年收入二三十万,很正常”。 30岁出头的王瑞,去年从江苏常熟回到家乡毛坦厂,扒掉家里的老平房,盖起一栋3层楼的“学生公寓”,“一年的房租收入远超过在常熟开服装店挣的钱”。但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他还是感叹:“我还是没眼光,盖房子太晚了。” 那些“有眼光”的当地人,敏锐地围绕着毛坦厂的强力“引擎”寻找赚钱的机会。 去年,金安中学新打开一扇北门,又为毛坦厂镇掘开一条积累财富的通道。短短一年间,新北门外那条命名为翰林路的水泥路边上,一座座四五层的小楼拔地而起,如今成为部分当地人的“摇钱树”。尽管由于工期紧张,有的楼房外墙还没来得及被白瓷砖填满,裸露着整面墙砖。 毛坦厂镇,正在以制造高考“神话”的毛中为圆心,划出一个中部省份山区集镇的经济图景。几乎与毛中崛起的节奏同步,毛坦厂镇的经济也开始有起色。这个土地面积紧张、工业并不发达的镇子,还曾在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挤进六安市经济发展综合实力20强乡镇。当地政府介绍,去年毛坦厂的财政收入将近1500万元。这个数字,是邻镇东河口全年财政收入的近4倍。 镇政府的杨化俊说,毛坦厂从过去以采茶和卖竹子为主“山口经济”,发展成为现在的“校园经济”。 在这个拥有明清徽派老街的老镇上,当地镇政府还想打好一张旅游牌。不久前,一条超过千米的明清老街路口,建起一家仿古徽派建筑的“毛坦厂老街游客接待中心”。但是这个崭新建筑物的棕色镂空玻璃门如今却紧闭着,门前还立着由三根竹竿搭起来的晾衣架,上面挂着女人的裙子和内衣。 相比于起步较晚的旅游业,由毛中带动的校园经济,能为毛坦厂镇带来更稳定的消费市场。杨化俊算了一笔直观的经济账:“毛坦厂将近3万学生和家长,如果保守估计,每人每天在镇上消费10块钱,全镇第三产业一天的营业额至少30万。” 有时,面对由毛中这台引擎发动起来的市场,毛坦厂这个小镇子也会应接不暇。那些无力承载的消费需求,就会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或者县城,成为周边地带的福祉。 70岁的本地人熊春义很难想象,毛中是如今镇子的中心地带。他更怀念上世纪60年代,坐落在毛坦厂李家冲村的“三线厂”,曾经为这个镇子增添的繁荣景象。 “三线厂”是特定年代的产物。在1964年至1980年,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巨资,号召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民工,在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建起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当年,毛坦厂这里建起一个生产枪支和汽车配件的军工厂。 9月初的一个下午,干瘦的熊春义老人,蹲坐在墙皮剥落的灰砖楼门口,一边搓着玉米棒,一边回忆起有关三线老厂的画面。他曾在厂区学校的食堂做工,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工厂搬迁到马鞍山之前退休。 那些记忆,就像熊春义住着的这栋三线厂老宿舍楼一样,已经很陈旧。 “那时,厂区是毛坦厂最热闹的中心,姑娘以嫁到三线厂为荣。”当然,他也知道,现在的毛坦厂人“以把孩子送到毛中上学为荣”。他的女儿在毛坦厂镇区生活,以租房为生计。 即使没有这个老人的回忆,如今看着遗留在这里的厂房、医院和学校旧址,以及墙壁上依稀可见的属于那个年代的宣传标语,也会引来毛坦厂年轻一代唏嘘感叹“不同时代的寓言”。 一位毛中的年轻老师说:“看上去这个厂区过去是多么繁荣。让我联想到毛中,如今这里也这么繁荣,但不知道以后会如何。看来真是要居安思危啊! 有关毛坦厂的一切 在毛坦厂呆了几天后,来给儿子陪读的汤才芳觉得,“这里没有新鲜事了”。 除了给儿子洗衣做饭,在毛坦厂剩下的大把时光,对她而言,只能用“无聊”来形容。 一到傍晚,小镇会热闹起来。三三两两的中年妇女,绕着毛中院墙外面的小路散步。随着天色越来越暗,零零星星的人,逐渐汇成川流不息的人河。 在路灯下随着音乐扭腰摆臀的人们,会给马路岔口制造一些拥堵,惹得汽车司机拼命地按喇叭。 毛坦厂镇的领导曾经表示,镇上将来要建一个专门供陪读家长们娱乐休闲的文化广场。 鳞次栉比的出租屋门前,头发湿漉漉的女人们围坐成一圈,谈着家长里短或者孩子的考试成绩。腆着肚皮的中年男人,将耳朵凑到收音机旁边,听着黄梅戏。 汤才芳想给自己找更多的事情做。她跟房东“搞好关系”,要来一块免费的菜地。她连夜翻了地,种上了大蒜和香菜。这个过日子精打细算过的女人,抱怨镇上农贸市场的菜价“太贵了”。 种菜开始成为一些陪读家长们所热衷的打发时间的方式。毛坦厂一些弃耕的荒地,被重新撒上了蔬菜籽儿。那些找不到整块荒地的人,只好捣腾起学校院墙外面的土。初秋时节,小镇时常弥漫着一股秸秆烧焦的呛人味道。 近几天,汤才芳在镇上找到活计。她在离出租屋不远的一个服装店里做缝纫工。晚上,当自己儿子正在教室里埋头苦读的时候,她踩着缝纫机的踏板,为这个小镇输入劳力。 在毛坦厂镇,有10多家服装加工厂以及官方都不掌握数据的遍布于大街小巷的小作坊。那些踩着踏板的缝纫女工,绝大部分是镇上的陪读家长。 “现在正值服装企业青黄不接的‘用工荒’,但是我们这里基本不愁招人。”毛坦厂镇上最大一家服装企业的王领班说。 为吸引陪读家长来做工,大部分服装企业和小作坊会在招工广告上写着:“工资计件,工作时间不受限制”。饭点之前,这些女缝纫工必须扔下手中的夹克袖子或者棉服内胆,赶回租屋给孩子做饭。 杨化俊欣慰地向外人介绍,一家上海的大服装厂,“看中我们这里有大量的陪读家长”,考虑落地毛坦厂镇。 汤才芳并没意识到,像她们这些来毛坦厂的陪读家长,正在改变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在她看来,除了儿子高考,其余消磨时光的活计,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她听说,毛中有一棵百年老枫树。很多家长和学生拜过这棵“神树”以后,“很显灵,第二年高考涨了一两百分呢”。 一天下午,汤才芳特意去寻访这棵“神树”。这棵老树长得枝繁叶茂,一根长长的树枝伸出学校的院墙。 走近毛中北门东侧的那面院墙,汤才芳很震惊。观世音菩萨的十字绣和“毛中栽培,神树显灵”的红色锦旗,被铁丝挂起来,几乎遮住大半面斑驳发黑的墙。褪色的锦旗旁边,一块简易房铁皮搭起的棚架下面,香灰堆到1米多高,一大片墙皮已经被熏得脱落,露出红色的裸砖。 汤才芳想烧上一柱香。巷子口,一个中年女人摆着香火摊,装烛火的纸盒上两个手写的大字清晰可见:“状元”。 这个陪儿子第二次冲刺高考的母亲,在巷子口停留了一会儿,还是转身离开了。她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一些迷信的甚至说不清的神秘感萦绕在毛坦厂。很多学生会在高考前放孔明灯,希望获得好运。但黄色是忌讳,因为那表示“黄了”。“送考节”那天,前三辆大巴车的车牌尾号都是“8”,出发时间是上午8点8分。头车司机属马,寓意“马到成功”。 如果真能熬到“马到成功”的那天,郑汉超考上了电影学院,这个未来的导演想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有关毛坦厂的一切”。 (应采访对象要求,郑汉超为化名)(记者陈璇)
·上一篇文章:“学霸经济”走红:分数至上的另一种表达?
·下一篇文章:“起跑线恐慌”并非矫情
转载请注明转载网址:
http://www.zjjr.com/news/jygc/1682314838HJEA3I6BB1GGH7I4JB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