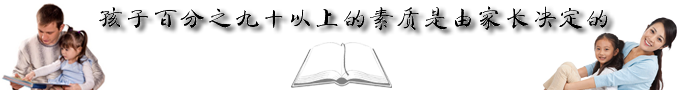网瘾治疗纪实:走出“13号室”
来源: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网 作者:兰天鸣
六
2010年的夏天,江一帆以为自己自由了。他以578分考上一所大学的采矿工程专业,当时正是国内煤炭需求正旺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可能被送回“四院”了。
江一帆说,他的父亲当时突然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神经疾病,卧床在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江一帆帮家里装修时总是偷懒,愤怒的父亲爆发了。
在几个亲戚的拉扯下,江一帆又回到了“四院”。
根据惯例,送回来的“再偏”的盟友要无条件地接受从严从重的治疗——每天进行一次更大强度电击治疗。
“四院”的盟友中不乏一些在读的大学生、硕士生,甚至还有年近40岁的中年人。江一帆这才发现,自由是这么的脆弱,只在家长一念之间的改变,到手的自由立马就会摔得粉碎。
好在10多天后,父亲又派人把他接了出来,并向他道了歉,承认当时自己的精神确实不太好。
江一帆接受了道歉,也学会了更高明的伪装。
上大学后,他和父母沟通的原则是“报喜不报忧”。大一时,他毫不犹豫就签下了一家在国内有多家分部的大型煤炭企业,当时正是煤炭企业用人的高峰期。他只想远离父母,远离山东。
除了过年,他几乎不回家,寒暑假骗家里说在外头打工,实际上就在寝室里打游戏。每月他靠游戏能赚4000元左右,以此支撑了他大学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就在江一帆一步一步实施他的逃离计划时,张旭同却筹划着如何结束这一切。
第二次从“四院”出来后,张旭同就再没回家,在老家的众多网吧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他说,他陷入到无休止的噩梦当中,梦里基本只有两个画面:在“13号室”被电击,以及亲戚在后面追赶他。第二天起床,他感觉就像跑了一整晚一样疲惫。
一次,他在酒店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正是关于网戒中心的专题片《战网瘾》。当张旭同看见画面上杨永信的侧脸时,他的大脑突然一下放空了。
等他缓过神才发现,自己已经把电视机砸了,每一个大部件都砸碎了。他说他事后赔了酒店3200元钱。
他开始寻找不那么痛苦的死法。买安眠药失败后,他听说降压药吃多了也能致死,更重要的是能在药店直接买到。
张旭同将5瓶降压药,200多粒,一把把抓着吞了下去。昏迷前,他给父母发了一条信息:“最后了,只想知道你们到底后不后悔把我送进‘四院’。”
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ICU病房里了,并查出来患有高血压,母亲在一旁照顾他,什么也没问,只是不断地叹气。
他找过心理咨询师,想吐露心声,却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倾诉的欲望”。在不了解他的过去的情况下,心理咨询师告诉他患上了抑郁症。
七
对于一些2007年、2008年进过临沂网戒中心的人来说,有些人成了成功的“精品”。
有人在欧洲读博士,有人考上公务员,有人进了苹果公司,有人进了央企,也有人成了军官,还有人耽误了多年的时光后,仍在大学里念书。当然更多的人销声匿迹,失去了联系。
尽管当时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但很多当时的盟友还是在“杨永信”吧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组成各种小群体。
在贴吧里,一名2008年的盟友晒出自己穿着佩有上尉军衔的军装的照片,留下一句:“我现在过得很好,杨永信我既不感谢你,也不记恨你。”
硕士毕业的刘思恩在“如何评价杨永信”的帖子里留下一句:“我不怪杨永信,也不怪我的父母,怪的是以前不懂事的自己。”有人跟帖评论他“脑子被电糊了”。
刘思恩说,当时央视拍《网瘾之戒》的时候他就在“四院”现场,他怕说错话,有意避开了所有镜头和采访。他认为《网瘾之戒》真实地反映了里面的生态。
他说,也正是那段经历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刘思恩还总结出了一个规律:“那些至今对‘四院’恨之入骨的人基本没啥大出息,而出来后真正认真读书的人,对那个地方不会抱有太大的负面情绪。”
在他看来,不反对“电击疗法”的《战网魔》和批判“电击疗法”的《网瘾之戒》这两部片子的角度都有道理。“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好坏留给后人评。”
曾经进出“四院”13次的谢坤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四院’并没有说的那么残忍和恶毒,想想里面有哪个孩子是善类,有哪个不是自私享乐不顾父母的?”
一些盟友以自己的方式避开那段往事。有人承认,自己那个时候确实年少无知,需要管束;有人警告记者,“不要骚扰我,只想安静地生活”;还有人无奈地说,“过去的伤疤就不要再去揭开,要不然只能破坏亲情。”
甚至还有盟友对记者说,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无药可救,只有送去“四院”这一线生机的话,他也会尝试这么做的。
有位女盟友读大学时选择了法律专业,想以宪法的名义,控告网戒中心侵犯人权,可最后自觉势单力薄而放弃。
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些电击治疗仪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恶魔,因为父母只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哪怕就是电也要电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她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网戒中心里,大多数人都被诊断为心理疾病或网瘾,但实际上不少人只是青春期的短暂迷茫,之后他们还能回到正轨,可那些因此堕落无法回头的盟友又该怎么办呢?”
一位盟友家长看了《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文章后倍感气愤。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假设你有孩子不学习了,和正常人不一样了,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着急。这个临沂戒网中心,是一个救孩子的好地方,并不是害孩子的。”
他说自己的孩子,曾经在家里只顾着玩电脑游戏,不和家里接触,脾气越来越暴躁。“作为家长,我已经用尽了所有方法,没办法才交给戒网中心来管理”。
在他眼中,孩子从四院出来以后,内心没有恐惧,回家就和他们沟通。还把打工挣来的钱,给爷爷外公各买了一箱酒,给外婆和奶奶买了手表。
可当被问道,如果孩子“再偏”,还会把他送去四院时,这位家长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不会再送回去,我的孩子已经好了,毕竟已经长大了。孩子的行为上有缺陷,家长自身也缺乏沟通,管理孩子的方法不当。”
8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访了网戒中心,门口一群家长在门口蹲守,还有人从附近的小车里给记者拍照。从外面看,网戒中心的每一层入口都被两道铁门紧锁着。
当记者试图进入网戒中心时,一些带着“xxx爸爸(妈妈)”名牌的人开始跟随和驱赶记者,表示“请你快点离开”。
记者试图通过电话联系杨永信,其电话处于关机状态。
据 8月22日《沂蒙晚报》报道,杨永信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如果没有患者,网戒中心一天也开不下去。网戒中心之所以能够存在到今天,除了其合理合法合规外,也是因为有众多的家长和孩子需要这个地方,如果有一天家长和孩子不需要这个地方了,网戒中心因此关门了,那将是我感觉最幸福的事。但现在,那么多的家长带着求助和无奈而来,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这份事业,责任和同情心是驱动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结尾
最近,张旭同看了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聚焦》。
看到其中一个桥段时,他不停地流泪:被猥亵男孩的父母知道牧师假借上帝的名义对自己孩子犯下罪行后,依然给牧师端上了一盘点心。
张旭同也曾试着与父母和解,但一想起那句“加大剂量,电死他”时,就放弃了。“我从来不怀疑,我的父母是爱我的,但是方式有问题,依旧不能被原谅。”
有一次喝多了,他给母亲打电话,提起过去的事情。母亲很惊讶:“过去这么久,你怎么还没忘!”
“他们好像并没有觉得那段经历对我有什么太大影响。”张旭同说。
这几年,张旭同和女朋友“造”过几个人,可最后也都“处理”掉了。他表示,他对做一个好父亲没有信心。
毕业后,江一帆去了离家2000里之外的鄂尔多斯,从事煤矿设计工作。
煤矿实行上50天班、休息10天的工作制,好让矿工能够有较长的集中时间回家看看。
江一帆几乎没有用过这10天假期回过家,而是去呼伦贝尔看草原、去中卫沙坡头看胡杨林。
每周,江一帆都需要下矿井四五次,检查自己设计的矿井工程实施情况。
即使到了深达500米、令人窒息的黑暗地下,他的内心依然充满安全感。“自己设计的自己了解,这比在‘四院’和父母的身边强多了。”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出于保护采访对象,张旭同、江一帆、刘思恩均为化名)
本文转自冰点周刊,微信号:bingdianweekly,作者兰天鸣
·上一篇文章:“家里蹲大学”是教育的倒退
·下一篇文章:“起跑线恐慌”并非矫情
转载请注明转载网址:
http://www.zjjr.com/news/jygc/1682711203KIAA6CAEF20JAC888JF2.htm
相关内容
|
高康迪 杨艳敏 | |
|
余建祥 | |
|
余建祥 | |
|
佚名 | |
|
程红兵 | |
|
佚名 | |
|
徐速绘 | |
|
佚名 | |
|
王立武 | |
|
佚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