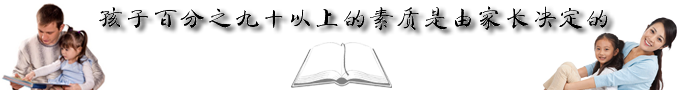我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人画展,是对此前15年绘画历程一次总结。此后,至今的21年潜心创作及理论研究,力图在中国画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所突破。《易传》和《老子》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辩证法传统的两个源头。《易传》和《老子》同样也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辩证法传统的两个源头。以“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 至“道”、“气”、“象”等, 将艺术情怀和哲学智慧的结合,成就了中国画的灵魂思想。在纷繁复杂的现代,我们追寻探索中国古代哲学精神,从“道”、“气”、“象”、“自然”、“虚实变化”、“淡泊致远” 中,探求中国艺术中反映民族与文化精髓的艺术表现“语言”。
艺术的使命就在于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找到适合的艺术表现。而人的心灵意志和高远旨趣,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都要表现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以诗书礼乐为根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浑然天成的大和谐。
老子和庄子都讲对“道”的观照,“道”是宇宙的本体和生命,道法自然,天、地、人和谐之美,作为中国艺术的灵魂理想,它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由流动,把自然作为最高的精神田园,从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时间与空间,将心中的意向情怀整合和梳理,从而达到一个平衡、和谐、有序的统一体。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历代有代表性的艺术大师多以山水为绘画语言:如宋代的范宽、李唐,元代的王蒙,明代的董其昌、沈周,清代的石涛、龚贤、梅清、王原祁等众多杰出大家多以山水抒写情怀。山涧小屋旁、小溪畔往往能见一人或两人,或对饮成趣,或静坐沉静在天地的美妙之中,从中领会超越自然与人生的妙道,无不体现了天、地、人之“道”。
“和”既是和谐、统一,也是艺术最基本的规律。一切艺术作品,也正是在自然世界反复调和中而产生的。所以才有庄子以和注《释德》,既是指人的本质就是和,正所谓“德者成和之修也”,人和上升为天和,庄子是以天“和”为“道”就是天地的本质,只有“和”才能生道,才能生万物,“生生不已”。但它不同于“同”,“同”是缺乏生命力的,它意味着单调一律,而“和”是能化异为同,化矛盾为统一,却又允许异物的存在,逍遥出尘世,驰骋于艺术的大美世界中。在此状态中,精神是大超脱、大自由,“乘云气,御飞龙”,”精鹜八极,心游万仞”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也就说,艺术创作是一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活动,其神凝与天地之间。这种思想自古以来就渗透在中国绘画艺术之中,因此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注重精神感应下的笔墨情怀,所谓:“神之动物,物之感人”。
在魏晋南北朝美学中,王弼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 。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美学命题。这个命题在《易传》“立象以尽意”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一个角度对“意”和“象”的关系作了深一层的探讨。这就推动了美学领域中的“象”范畴的转化,意味着人们对艺朮本体的认识,已不再停留在抽象的笼统的阶段,而是已经深入到了一个更为内在的层次。这在美学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又于南朝画家宗炳提出了“澄怀味象”、“澄怀观道”,是对老子美学的重大继承与发展。他把老子美学中“象”、“味”、“道”、“涤除玄鉴”等范畴和命题融化为一个新的美学思想,对审美关系作了高度的概括。他提倡“以神法道”,即以思维的精神去探求乃达到体现大道的真质,他強调物我之间的精神感应。这在美学史上是一个飞跃。
在审美意象方面,唐五代书画美学家提出“同自然之妙有”、“度物象而取其真”等,从而把“意象”和“气”这两个范畴联系统-了起来。他认为绘画的意象应该表现宇宙的“气”,做到“气质俱盛”。做到了这一点,就称之为“真”,或称之为“自然”。张彦远提出了“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这十六个字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是说在审美观照时排除一切故有成见与杂念,重在物我对话之精神感应,从而到达一个超然的精神世界的领域。
我看过匠人画画,先打好格子然后再将其内容填进去,悬于壁上、殊觉蹩脚。高明的画家、把一张纸作为太空,赋与其彼时彼地殊有的精神情感,在无边无际的太空自由地弛骋,从而画家的笔墨所产生了点、线、面、叠加、渗透、摩擦、转折,行笔的缓急、轻重、粗细,用墨之少所产生的光涩、枯润、厚薄等种种效果。这些效果引出的刚柔、媚道、老嫩、苍秀、生熟、巧拙、雅俗种种感受,使得技巧的虚与实、巧与拙、繁与简、疏与密等矛盾双方达到了和谐统一,对立的概念成为相反相成的统一体,合乎天之造物。这就是笔墨与精神之大“和”。
古人筑起高壇祭或拜将、并非单是讲排场,这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精神感应的学问,从登上高壇、昂首环顾、凭虚御空,其气场放射外延、承天接地,以宇宙为舞台的強大精神力量和诸多的美好向往由然而生,把有限与无限结合起来,把定量与无量溶为一体,这便是中国的美学与哲学的统一。画家应俱备高层次的对“宇、我’”的认识,“以神法道”为什么会“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山水画家高层次的审美要求,不是即景描写式,而是精神感应,“物我通达”,贵在精神感应,我之精神賦与物、物之精神感呼我,与精神“电波”之传导,画家与大自然精神感应最強的信息得以体现就是艺朮。精神感应指高层次审美而言,“与天地同德”、“与阴阳同波”,决非看到金色落日想到鸡蛋黄一类庸俗联想。
中国画最大的特征就是以有限的笔墨空间表达无限的“意”与无限的“象”。中国画的意境是什么呢?意境也可称之为有情之境,因为它是由审美主体和客体各种矛盾的复杂关系的构成,它属于比形象更为丰富的美学范畴。画家按照自己的理想将生活中的实景用美的形式在作品中表达出来,形成一种能够引起共鸣的艺术境界。这种意境,文学上是所谓的“意外之意”,而绘画中往往是“象外之境”虚实相间,重在自身的体会与精神感应,强调内心的主观情怀与自然物象的交融、升华,它所呈现出的独特的空间包容了人类心灵与自然宇宙最深处的生命境象。意境的创造最重要的是画家必须有一颗能体悟宇宙本原的诗心。现实世界中的人物鸣禽、虫鱼走兽、山川草木、江河湖泊、流云烟雾等自然物象,才是真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蓬勃无尽的创作源泉。中国哲学重视自然,对宇宙人生之道的把握,实际上是凭一种浸透着主体生命意识的诗性直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多带有浓厚的诗人艺术素质,而中国诗人的灵性从来就蕴含着一种悠悠的形而上情怀,中国哲学是诗性的,中国艺术是高妙的。在世人看来,国画作品所表现的是一种飘飘欲仙的理想王国与人类的不受世俗污染的真性情,仿佛是艺术家追求的一种出世情怀。作为中国哲学而言,它本自很难界定,既是现世的又是出世的,它关心的是“不离日用常何内,直到天地未画前”。这是理想主义情怀的追求,体现在哲学家和艺术家心中,便成为对人生理想不断的追求。正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不断地操练自己,生活在哲学的体验中,超越在自然与自我之间,以求天人合一。这种操练一旦停止,自我就会抬头,内心的宇宙意识就会丧失。所以为了达到圣人的理想,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永远不会懈怠的。这种情怀自然体现在画家的笔墨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即富于暗示但却不是一览无余,这也是中国绘画所追求的艺术目标。暗示的语言是如此不明晰,但是所蕴含的几乎是无限的。在《庄子》的《外物》篇中这样说道:“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充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充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是无形的,但他又是个参照“物” ,“道”更是人类思想灵魂的精神支柱。按照道家的思想,道不可道,只能暗示。笔墨的作用,好比语言,不在于的固定形态或含义,而是在于它的暗示,引发人们去悟道,引发人们去分享个人的所得,个人对待整个世界大美的态度。我认为:局限笔墨的所谓线条技法,浓淡于湿,其实都应该在完成它们的暗示作用后而忘记,不要让人被并非必要的形式语言所拖累。近些年来,对笔墨的争论喧闹如此,其实不过是闹剧一场。我们所关心的不应是笔墨本身的状态,而是讨论真正的内心世界。虚与实就是一个宇宙观的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认为:宇宙空间是个太虚之境,太虚凝而成气,气聚而成物,物散而为气,气复散而太虚。自然宇宙是气与太虚的统一,即物与空气的统一。我们知道虚与实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美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有形与无形、主观与客观、直接与间接、有限与无限、思想与意象等等,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我们读古诗词,比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或是“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体会到的往往是言外之境,弦外知音,让人如入一个具有“境中之境、飞动之趣”的艺术空间,画诗同理。所谓境生与象外,艺术意境有“象”与“境”两个不同层次,由实入虚,由虚悟实,虚实相对,有者为实,无者为虚,有据为实,假托为虚。笔是有形的、墨是无形的,画面是有形的、画中灵魂是无形的,有形为实、无形为虚,客观为实、主观为虚,具体为实、隐者为虚,学前为实、未来为虚,已知为实、未知为虚等等……直觉中看不见摸不着,却又能从画面的笔墨与空白中体味出那些虚像和空灵的境界。点点墨迹和画家苦心经营的看似不经意的空白,淡淡的几缕云烟,疏疏的几尾秋苇,或为江湖,或为深水,天地一体,渐入渐出,空灵之气跃然纸上。这正是“天地之间,其犹乎,虚而不屈,动则愈出”即“风箱”,天地犹如一个巨大的风箱,充满了“气”能使万物流动,生命不竭,车轮中心孔是空车轮方能转动,杯子中间空方能盛物。“气”是表现体以外的“虚”,没有“气”作品就没有生命。在中国画的意象结构中,没有虚空、空白、其意境难以体现。中国画的“妙境”与“空灵”,追根溯源可以称之为“道”。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被视为生命最终极的本根,它也是中国古典美学观念的原型。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是天地产生之先的原始混沌,它是万物形成之母。天从命名,我们称“天”为“道”时,这个名字只是一个指称,正所谓“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此系老子的一种倾向,他认为“气”与“象”之间才能产生紧密关系。审美是对有限的“象”的观照,进而实现对“道”的观照。庄子说的“心斋”“坐忘”,都说明先要做到“澄怀”才能“味象”“澄怀”就是“坐忘”,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有虚静空明之心境,才能实现对宇宙本体和生命的审美观照,即对“道”的观照。
我认为一个画家应该注意“虚静”之天性,审视“气与象”的紧密关系,在“澄怀”的状态中去创作。只有静下来才能进入高层的思维阶段。“静则定,定则安,安则止”、“知其所止,止於至善”,正所谓定生慧,一切最美好的品味、向往、启发、追求尽在其中了。黑格尔说:思维着的精神是最美好的。这和中国美术崇尚静美是一致的。其创作的作品,不在外而在本身的精神之内。此时再加手法去创造,不是以主观去追去客观的形态,而是用自己的手、自己的笔墨实现自己精神中的“形与意”,这样才能毫不歪曲地进入虚静之心的“表象”,这样主客观合一的创造也就无怪乎可以“惊扰鬼神”了。宋代画家郭熙将这样一个审美的胸怀称之为“林泉之心”,所谓“胸中宽快,意思悦适”,正是此意。唐代美学家提出“境生于象外”,进一步道出了“境”作为审美客体,比“象”更能体“道”。意象必须表现宇宙的本体和生命,作品才有生命力。南朝谢赫提出“气韵生动”的命题,就是这一思想的概括,它几乎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画的最高美学法则。
当一切喧嚣归于沉静,自然之心归于淡泊。老庄皆以自然为’’道’’的特质,以为自然脱俗方能悟道。只有去除一整套繁缛因明,才能外静内净,方能直指人心。万物以自然为美,至丽之极,而反若平淡;正因为如此,虽然艺术必然要求变化,虽然凡是生命的东西必然有自然变化,但是没有淡泊的心灵,就无法窥视到对象的精神,画的再是尽诙怪异之变,也是死物而已。所以作画时又须“无心”,即无心计较表达精神以外繁锁外形的过分的雕琢,写似无心、实责重意。似八大山人“于无心处写鱼、于无鱼处求美”,历代绘画大师所以知画,所以能创作有飞扬生命力的作品,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保持一颗淡泊的心灵。
王国维在分析古典艺术成就时说,“最纯粹之文学,若自其思想言之,则又是纯粹之哲学也,唯此其纯粹,故哲学与艺术通而为一,纯粹乃指哲学与美术为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因为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
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
上一篇:“传统文化”更需知者传承
相关推荐